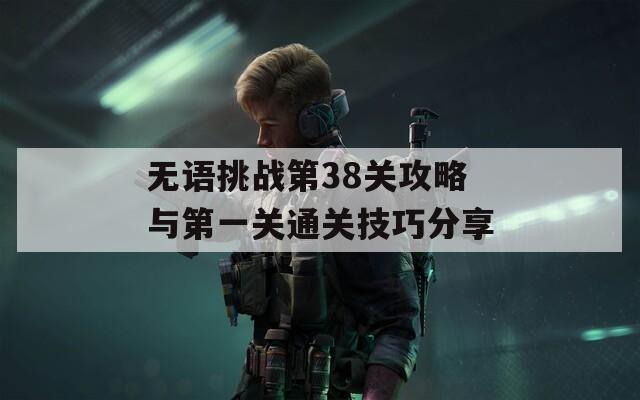白鹿原电视剧:黄土高原上的家族史诗与人性博弈
作者:玉康游戏网
发布时间:2025-03-04 14:35:30
官方推荐
抵制不良游戏,拒绝盗版游戏。 注意自我保护,谨防受骗上当。 适度游戏益脑,沉迷游戏伤身。 合理安排时间,享受健康生活